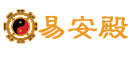做梦梦到麻雀(做梦梦到做梦醒不来)
李力,新疆作家协会会员,襄阳散文社理事。作品曾发表于《西洋》、《湖南文学》、《百篇散文》、《诗歌周刊》、《诗歌月刊》、《绿风》等刊物。现就职于鄯善县文联。
我是谁?我与世界、与我有什么关系?这些问题从一夜又一夜开始。漆黑的夜里,除了星空,月影,地影,还有我一个个零碎渺小的梦。
一
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。在荒野的空地上,我在月光下和他们一起玩沙袋。她是中间的选手,我的对手。我是扔沙袋的那个。小沙包不停地从我手中飞出,恨不得把她打倒,使出浑身解数。沙包在空中旋转飞舞,最终被她接住了。谁能接住沙包,谁就是“英雄”,在下一局的开场就占据绝对优势。能够和“英雄”成为一家人,是玩沙包游戏时最大的愿望。我站在一群等待分配的人的外围。刚才拿到沙包最多的“英雄”成了主持人,分配了人数,一边四个人。“ 她举起双臂对准了我,小沙包在她的指挥下朝我跑了过来。我双手抱住它,蹲下来,紧紧地抱住沙包。就在这时,人群中一片欢呼。我受宠若惊,激动万分,我更加努力地追着那些飞来飞去的沙包,在这空荡荡的黄昏里和沙包一起飞翔。
我仔细辨认,她竟然是第一轮游戏的“赢家”。她“救出”了一个又一个被我击落的“牺牲者”。她是我最害怕的对手,现在她成了我的“盟友”。我看得很清楚,那女孩就是芳。方身材高挑,短发。她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。她莽撞,敢说敢做,像一只快乐自由的小鸟,盘旋在我身边。但是我和她完全相反。作为家中的长女,我承载着父母对生活的希望。我要好好学习,照顾好弟弟妹妹们的生活。芳成了我儿时最好的朋友,她所拥有的一切,是我年少时最大的向往。村庄在暮色中卸下一天的疲惫,灯光一寸一寸地暗下去,房子也跟着灯光越来越小,最后消失在夜色中。这并不影响我摸黑回屋,拿起杯子喝水解渴,又拿出一块前几天偷偷藏起来的水果糖。有时候觉得那些黑屋子比妈妈还亲切。他们不会催我回家,不会催我吃饭,不会催我写作业,不会因为弄脏了我的新衣服而惩罚我。他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我的一切。直到他们在葡萄田里耗尽了最后一缕阳光,我的父母才想起我放学回来。而此时此刻,我正在某片空地上享受着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太阳躲进山里,世界变得柔和。“天快黑了,让
在梦里,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在阳光下进行的,而是有光的。我选择性地看到了一些人的脸,听到了我想听到的声音。抱住那个小沙包的那一刻,我仿佛拥抱了整个世界。醒来时,屋子里一片漆黑,我躺在巨大的黑暗中,楼房在地上,“天快黑了,我要回家了”,耳边又响起了妈妈的叮嘱。没有梦到妈妈,这又是一个久违的梦。我和我的房子飘回了村庄的黄昏。弗洛伊德说,任何梦都可以分为显性梦和隐性梦。外观是梦的外观,是人们可以记住和描述的内容,类似于面具;隐藏的形式是梦的本质内容,类似于面具下隐藏的真实欲望。梦想是生活中隐藏的真相。它也有童年、青春期、青年期和成年期。一夜之间,我从少年无缝过渡到成人。以成年人的身份和思维体验童年的事情。
二
三道身影模糊,笑容清晰,正在争论着。好像和我有关做梦梦到麻雀,又好像和我无关。他们一个讲,一个听,另一个不时补充。他们会时不时地看我一眼,与我四目相对,然后瞬间移开,好像在躲避什么。我试着观察他们的嘴型,想弄清楚他们说的话是不是和我有关,可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,也无法靠近他们。梦里,我陷入了白天的焦虑之中,不停地回忆着与这三个人会面的所有细节。这三个人,一个是我的领导,另外两个是我的同事。他们一改往日冷漠的态度,津津有味地做出判断。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只有四个人,我就是他们三个。我是“审判者”和接受者,他们是决定者和宣告者。我平静地等待着宣判,没有一丝焦虑和担忧。我期待的是一个结果,而不是事件的原因和过程。前面的三个人转过身来,对我和善地笑了笑。我选择无视那些笑容和意味,怀疑刚才回避我的讨论。我终于找到其中一位,说服他把刚才讨论的问题和结果告诉我。准备好接受一切,梦醒了。毕竟,我搞不清楚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否与我相关,只好作罢。等夜幕降临,继续下一个梦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,也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个梦想。那个梦经常让我想起。“醒醒,是梦里跳出来的伞。” 诗人说。我从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影。
与世隔绝的古镇里,人世背景陈旧,岁月陈旧,岁月陈旧,人也陈旧。巷子又深又窄。快要追上那个影子的时候,我放慢了速度,慢慢来。终于赶上了。我们两个挤进狭小的空间,一起往前走。还没来得及打招呼,还没来得及看对方的脸,我就从梦中惊醒了。我遗憾地闭上了眼睛,想要重新连接到梦境中,哪怕看不清面容,只听声音就好了。梦回不去了。只能在梦境之外继续想象。之前,我只是觉得这是一场梦。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。你看得清楚的,是你走过的路;看不清还想看的,是没走过的路。为了从后面追上那两个人影,我跑了一个晚上。结果还是没追上。其中一个背影是我很好的同学,我也尽力帮助她。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时,对我视而不见。在梦里,他们总是走在我的前面。偶尔我能听到他们的笑声。从他们背影的动作来看,他们是在讨论一个问题,并且有着很多相同的感受。他们不时亲密地碰碰肩膀,不时回头看看身后,却无视我的存在。我很想验证或探究他们所讨论的话题以及不认识我的真相。我必须赶上他们。如果我追上他们,我应该问什么?你问他们为什么不理我 不认识我?但是会有答案吗?我可以问出口吗?面对熟悉的面孔,陌生的眼神,应该很难开口。在分析判断的过程中,提问的勇气消失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在我的视线中远去,消失在我的梦里。我在沮丧的状态中醒来,问自己在梦中我不能再超然了。你应该只关心与你有关的事情,而忽略与你无关的事情。那两个身影和现在的自己是什么关系?在梦里,我好像是个导演。剧情、人物、情节、结局都是我自己把控的,但我还是造不出一个完美的自己。在分析判断的过程中,提问的勇气消失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在我的视线中远去,消失在我的梦里。我在沮丧的状态中醒来,问自己在梦中我不能再超然了。你应该只关心与你有关的事情,而忽略与你无关的事情。那两个身影和现在的自己是什么关系?在梦里,我好像是个导演。剧情、人物、情节、结局都是我自己把控的,但我还是造不出一个完美的自己。在分析判断的过程中,提问的勇气消失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在我的视线中远去,消失在我的梦里。我在沮丧的状态中醒来,问自己在梦中我不能再超然了。你应该只关心与你有关的事情,而忽略与你无关的事情。那两个身影和现在的自己是什么关系?在梦里,我好像是个导演。剧情、人物、情节、结局都是我自己把控的,但我还是造不出一个完美的自己。你应该只关心与你有关的事情,而忽略与你无关的事情。那两个身影和现在的自己是什么关系?在梦里,我好像是个导演。剧情、人物、情节、结局都是我自己把控的,但我还是造不出一个完美的自己。你应该只关心与你有关的事情,而忽略与你无关的事情。那两个身影和现在的自己是什么关系?在梦里,我好像是个导演。剧情、人物、情节、结局都是我自己把控的,但我还是造不出一个完美的自己。
秘密是隐藏的花开在许多黑暗的地方,我在花的影子里奔跑,找不到边界
那天晚上,我用诗歌记录忙碌的自己。
三
这两个朋友是我生命中最舍不得失去的人,或者说我不想失去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。一个人的脸很清晰,一个人的脸很模糊。清面人嫌我吵,我立马不再说话,隔绝了所有的声音。那个人经常输入我的文字,他输入文字的时候大多是沉默的。在梦里,我们回到男孩身边,走在一条小巷里。褪色的雕花门,锈迹斑斑的门铃,古老的桑树和杏树从门楣上伸出来迎接我们,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我们年轻的身影上,镜面般的天空是湛蓝的。我和他一前一后地走着,偶尔抬头看看天空,偶尔看看对方。不远不近的距离,让梦里的旅途不觉得寂寞。我把这当作一次真实的体验。但这是一个梦想,因为我们没有一起度过少年时代。那个脸模糊的人,我不记得曾经见过他或以任何方式帮助过我。我只记得打电话给他哭着说我的委屈。他在电话那头呼应着我的义愤填膺,默默陪伴着我。到底是什么让我如此伤心难过做梦梦到麻雀,我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那个漆黑的夜晚,一些温暖的慰藉。于是我把梦搬进了文字,把文字中的静止变成了动。我把他定为我梦中的主人,希望他一直都在,可是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。时而他是青梅竹马,时而是少年时的暗恋对象,时而是他在清晨阳光下成年后的背影…… 梦想和现实有关系吗?记忆是对世界存在的某种形式的确认,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。
梦想也是一种生活。当我想明白这一点时,突然觉得自己浪费了睡眠世界中许多美好的时刻。“我开一辆服从我的车” 辛波丝卡的梦想是一辆服从他的车;“如水,行于根茎,游于奇异城邦”,阿多尼斯的梦行于根茎水;“醒醒,是梦里跳出来的伞” Transtram的梦是一把伞;“天地一指,万物一马”,庄子用“一指”把天下万物变成一个整体;而我也一直把不如意、灰暗、不务正业的自己归咎于黑夜,把自己从未过过的生活归咎于梦想。一种消极的逃避,在其中可以找到世界的和平。在一座古城里,我走过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,街上的人既陌生又熟悉。陌生人微笑着打招呼,熟悉的人各假装各怀心事。我住在临街的小二楼。当我离开房间时,我清楚地记得楼梯的确切位置。和模糊的朋友逛完夜市回来,再也找不到楼梯的位置了。入口完了,手机也不见了。每个人都很忙,没人关心我在找什么,能不能回家。我并不着急,只是在土墙周围闲逛,喧嚣的世界一切如故。古城街道两旁黄泥砌成的城墙古朴随意,每面墙上都刻有古字。我不觉得奇怪。偶尔会碰到几个熟悉的影子,眼神感觉很陌生。是H,她在心里默念着自己的名字。她可爱又可怜的形象永远是男生眼中的林姐。
此刻,她正和一个男人一起走在古老的街道上。那是Z,他拿了我的作业还没有还回去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是L,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。“喂,W老师,你怎么来了?” 我既兴奋又惊讶,和一位许久未见的文友打招呼。他抬起头,转身,轻声问道:“你是谁?” 意识到自己的不礼貌和鲁莽,我略带歉意地指了指不远处的办公室。我是刚来的XX。春光透过玻璃照在古铜色的桌子上,几只麻雀在窗外叽叽喳喳地叫着,目光的交汇处闪过一丝阳光,融汇着温暖,像是青春里的某种想象,我把他比作那个《春天的清晨》,定格为某篇散文的开头,常常翻开阅读,怀念。这些人此刻全都聚集在了我的视线之中。我继续寻找楼梯间。这时,来了一个瘦瘦的男人,我好像认识他,他又不认识他。他搬走一张面无表情的旧椅子,楼梯出现了,等我松了口气上楼时,才从梦中惊醒。因为工作,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。刚来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走错巷子,找错楼,走错楼层。我每天用不同的错误去熟悉这个我并不陌生的小镇,同时用心表达我对这里一切的亲近。我首先靠近一条路,一所房子,一张床。在所有的亲密感中,我正在寻找一种安全感,这种安全感是从锁门开始的。在租来的房间里的第一天,我把自己锁在屋子里。我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那天的经历:
经过两天的擦洗、修理、更换,原本是别人房间的房间,按照我的意愿一一整理。因为是老房子,一些设施的功能已经被岁月磨损,回归到最原始的功能,也就是我现在描述的锁。第一天,我搬进了一个陌生的房子。我尽量缩小空间,保证自己的安全感。我满意地锁上了每一扇门的锁。咔嚓咔嚓的声音让我心安。世界上没有比铁更坚固的防线。我分别锁上了防盗门、客厅门、卧室门。我记得进门的时候玄关灯还开着,出去的时候用力拧了卧室的门锁。发出清脆的咔嗒声,我用力拉门,但门却纹丝不动,而且锁着。我没有放弃,使出浑身解数去拧锁。我的手被划破了,指尖的鲜血粘在锁上,锁也无动于衷。时间静止了,锁不再是锁,变成了一块铁。我如梦似幻地面对着这个现实,锁和门合二为一,站在我的对面。我开始自助。仅用钥匙、修眉刀等少量小工具,将一把锁的可拆卸部件拆下,锁芯仍牢牢守住职责,牢牢插入与门相连的钥匙部件中。拆不开,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无奈地看着这小铁片,它正在宣告自己的锁的职责,在我无助的世界里像个巨人一样站立不动。我只能接受我被锁在屋子里的事实。第二天,找专业开锁公司开锁。开锁大师用了他所有的开锁工具来打开门上的旧锁。他说这是最早的防盗锁,应该有二十年的历史了。我说,差不多吧,这是老小区了。他说越老的锁越牢固。当师傅一丝不苟地开锁时,我正在向一把锁坦白自己对世界的疑惑,对陌生环境的不信任。这个开锁器是梦里帮我搬椅子的陌生人吗?开锁大师用了他所有的开锁工具来打开门上的旧锁。他说这是最早的防盗锁,应该有二十年的历史了。我说,差不多吧,这是老小区了。他说越老的锁越牢固。当师傅一丝不苟地开锁时,我正在向一把锁坦白自己对世界的疑惑,对陌生环境的不信任。这个开锁器是梦里帮我搬椅子的陌生人吗?开锁大师用了他所有的开锁工具来打开门上的旧锁。他说这是最早的防盗锁,应该有二十年的历史了。我说,差不多吧,这是老小区了。他说越老的锁越牢固。当师傅一丝不苟地开锁时,我正在向一把锁坦白自己对世界的疑惑,对陌生环境的不信任。这个开锁器是梦里帮我搬椅子的陌生人吗?我把对这个世界的怀疑,对陌生环境的不信任,都交代给一把锁。这个开锁器是梦里帮我搬椅子的陌生人吗?我把对这个世界的怀疑,对陌生环境的不信任,都交代给一把锁。这个开锁器是梦里帮我搬椅子的陌生人吗?
四
另一个模糊的身影第一次进入了我的梦境。也许他在某个时候也想到了我?否则我怎么会梦到他呢?我们没有交集,我居然可以在梦里遇见他。我用梦想去开拓世界,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愿望。我对我的朋友说,我昨晚梦见了你。朋友会高兴地说,谢谢你,你还可以梦见我。更多的梦想我不敢告诉别人,只能自己去想。这么多年,梦里的内容一直在重复。比如我经常梦到自己从高处掉下来,淹死在水里,失去孩子……这样的场景我已经反复梦到过。我们穿着蓝色的校服,背着书包,吃着冰棍,在夕阳下缓缓地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。我们没有说话,土墙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。世界是单一的,和平的。我们好像刚放学,又好像出去郊游了。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,要做什么,完全没有任何提示。在梦里,我看到了我的背影,美丽而纯洁。在梦的世界里,静静的享受慢时光,不思过去,不思未来,只忆当下。虚幻中的真实存在比现实中虚幻的存在更真实。这件小作品让那个夜晚变得美丽而梦幻。我知道我在做梦,我不想从梦中醒来。梦还醒着。梦的内容让我记忆犹新。第二天傍晚,我站在窗边,看着不远处的学校。那些走在校园里的身影,正是我昨晚梦见的样子。他们三五成群,有说有笑。两个少年一起推着自行车出了校门,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。
他们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,小心翼翼地交谈。初恋的年纪,羞涩,诱惑,拘束,充满想象……我把他们的身影搬进梦境,为曾经荒芜的青春添砖加瓦。他在书里一遍又一遍地讲梦里的事。他提醒做梦者,赞美织梦者,说做梦是自由的,美丽属于世间每一个人。但他将梦想一段一段地剥离,将梦想完全付诸现实。读了他的书,我才明白人是为梦想而生的。他说,如果你用梦想填满你的智慧、生命和生命中仅剩的那一点光阴,你的人生就会完整。我想我快到中年了,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无目的的徘徊,对生活的敏感度越来越弱,我不再为一片落叶而伤感,为离别而哭泣,为意外而庆幸,更多的是奔波于深不可测的世俗世界。我有很多业余时间和很少的业余时间。看了他的书,我好久没有做梦了。很快我又开始做梦了,在梦里我比以前更自由、更宽容。我喜欢的人和我不喜欢的人都可以进入我的梦境。喜迎所喜,所不喜则礼。“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底梦想着自己强大的帝国:男男女女都臣服于他,人们崇拜他——成为有史以来最高贵的梦想家。” 在他的话里我遇见了自己。我效仿他,梦想成为主宰一切的统治者,但最终没能达到这种境界。梦中的自己,依旧像白天一样犹豫不决。看到一些人就会紧张,看到不喜欢的人就会远离。我还是观众,不是主角。按照他的说法,我梦想的空间会越来越小,想想都会难过。大多数的梦都是悲伤的。
五
母亲又一次被父亲气得走出了家门。她需要向我倾诉并从我身上找到平衡。四十多年来,她从未停止过对父亲的“指责”。这是她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唯一的“事业”。你自己就是农民。你能天天靠跳舞、写字、画画为生吗?母亲对父亲的指责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,改变的只是她日渐衰老的身体和越来越幼稚的做事方式。那天晚上,在我的梦里,妈妈突然变成了年轻的身体和苍老的心灵。当她“控诉”父亲的时候,她的表情平淡无奇,不再抱怨。渐渐地,她弯下的背伸展了许多。年轻的时候,她有足够的力量平衡自己的世界。所有的委屈和指责都融入了姐妹俩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的注意力,她无暇顾及自己的世界。当我们的姐姐长大了,有了自己的生活,不再需要她的时候,她才慢慢回到自己的生活中,才发现自己这一生积攒了那么多的委屈。除了累了她一辈子的葡萄田,就只有和她闹过、闹过一辈子的父亲。父亲成了她怨气的来源,成了她发泄怨气的出口。那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深渊。梦里妈妈在指责爸爸无缘无故批评小妹妹,说她不听话,不会省吃俭用。妹妹是她大部分时间都和父母在一起的人。看着我的父母像孩子一样争吵,似乎让我重新体验了我的生活。做梦者说,我们不能完全窥视自己的梦,它是一种与我们同行的生活,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去梦想,也不能完全记住它,它只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充或隐喻。我们可以弄清楚的是,白天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我们选择忘记,但在梦中我们努力记住。
六
“我慢慢地抬起脚,又轻轻地放下。脚下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,半埋在沙子里……” 去了迪卡内村后,我不断重复着这个梦,一直持续了好久很多年。最后还是去找了梦里出现的地方。据史料记载,这里曾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致所在地。现在有了新名字叫“玛瑙滩”,很多石头爱好者都去那里捡“玛瑙”。捡石头的大多是中年男人。他们几乎是痴迷于在炎热的戈壁滩上一块一块地捡起石头,汗流浃背,用粗壮的手轻轻地擦去石头上的泥土,有的甚至用随身携带的手提包。矿泉水冲洗他们手中的石头,而他们专注于与石头的温柔对话,仿佛在寻找前世,也在寻找今生。这是我无数次梦寐以求的地方。我缓缓抬起脚,又轻轻放下。脚底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,半埋在沙子里……时间的每一个关节都仿佛踩在脚下,每一次放下,脚都能随着时间迈出一大步,从从古到今,又从今回到远古。我不知道哪块石头承载着我梦想的开始,哪块石头是我,我是哪块石头……“任何一块石头,任何一块上面的云;任何一天,任何一个夜晚,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,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存在,”辛波丝卡说。我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,那些精美的石头和我,那些精美的石头和我,都是这个世界的存在。我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同时存在。每当想到这个命题,我就会陷入自卑或焦虑的泥潭中无法自拔。
面对广袤无垠的大地,找不到如细叶石般恒久的姿态。走过忙碌的生活,为自己戴上不同的面具。假装像那些小石头一样,隐忍而执着。被烈日炙烤的荒原,吸收着白天天地的阳气,寂静无声。夜幕降临,整个荒野都在骚动,风吹过,地上的碎石发出细细的响声,我感知着这一切。晚上,我喜欢在昏黄的台灯下翻开历史书页,通过文字穿越更古老的世界。我眼中的荒地立即开始重建。五千年前或更早,这里就有人类的足迹。如果我回到那个时候,我一定是一颗细叶石或者正在成型的玛瑙石,不需要过多的语言表达,只要它安静而真实地存在即可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会进入梦境。这是一个醒着的梦,它就像戈壁荒漠中的一株孤草,在某个时刻被遗弃在荒野中,独自生根发芽,独自生长。我也偶尔拜访别人的梦境。在追风筝的人中,卡勒德·胡赛尼 (Khaled Hosseini) 建立了一个充满同情和救赎的梦想。哈桑哈哈大笑,对阿米尔说:“在梦里,你什么都能做。” 他让这个命运悲惨的少年在他的梦想中闪耀着人性和善良的光芒,让他做到了世人做不到的事。免于邪恶的救赎。庄周与蝴蝶在梦中互换身份,借梦诠释天地万物合而为一。这个梦想持续了数千年。人的一生,就是与自己的对话。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:一个感知和体验世界的自己,属于白天;另一个想象,理解和表达,属于黑暗和阴沉的夜晚。当生命走到尽头时,两个自我合而为一。人的一生,真的就像一场梦。(刊于《西部》2021年第3期)
《做梦梦到麻雀(做梦梦到做梦醒不来)》来自网络或者会员投稿,只为了传播更多内容,不对真实性承担任何责任,如内容有侵权,请联系本站,请来信告知,我们第一时间删除!